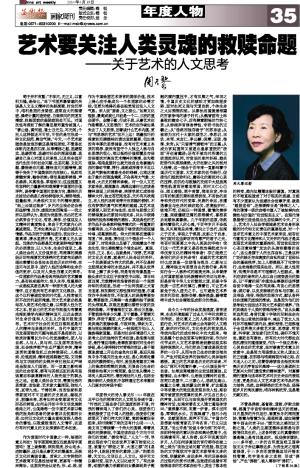艺术要关注人类灵魂的救赎命题
——关于艺术的人文思考
荀子并不言重:“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也。”当下书画界最普遍的失误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失缺凋蔽,时尚沉浮中,唯利是图的贪婪症、虚荣自大的摆谱症、操奇计赢的造势症、白眼相向的同道互搏症、权钱面前的垂涎症到处可见。对国民性有深刻了解的鲁迅曾郑重告诫国人:“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个别人这样做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形成一种文化规范、舆论气候。”今天,一个艺术家随你是放浪形骸还是循规蹈矩,不管是在体制内还是在江湖,如果樗栎之躯,逃避现实、逃避苦难、逃避对社会的深层观察、逃避自己良心对道义的承担,以及完全抛开当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善恶是非问题、精神追问问题等等,就等于丧失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核心。纵然有唐髓宋骨,翰林流韵;哪怕是溢彩锦绣,声名鼎沸,风高浪急、草寇称王;这些捏塑又有怎样的力量影响和混淆着中国画的价值评判,误导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最终的历史结论必然是几株枯树临秋风,颓势难挽,掂量起来,只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纸上云烟过眼多”,岁月的尘埃必定会将那些矫情、伪诈、虚假的东西淹埋——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坚信:杰出的艺术必然来自于文化、哲思、美学、价值观及人文精神的高度契合,来自于艺术家内心的真诚表现。艺术如果失去了内在的诚实与情感,作品则流于浅薄与虚伪,犹如沙土上建高塔,清水里捞月亮,艺术意义无从谈起。优秀的作品都是艺术家某种特定情绪的必须表达,以人为本,生命价值至上,是人类社会的人文价值所在,有深厚的美感经历即有深厚艺术修养的艺术家有足够的理由秉着社会良知去回应历史的呼唤,在追问与反思中,进行人性的诠释和生命价值的剖析,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一位画家的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是否能卓越伟大、恒久永存,很重要的一点是视其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这才是所有艺术家的文化根脉。在这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人性常被无所不在的利益所掩盖,而大艺术家必然是站在人类艺术伦理之巅,以探索人性为艺术之本,把自己的艺术创作拓展为有着高尚深刻美学内涵的精神追问,以此去表达对生命价值和人文主义价值的极致追寻。艺术对于社会的关注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关怀。当代中国的文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不是局部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以及原有政治伦理、社会秩序都产生出严重的冲突,精神迷惘和道德危机正在持续恶化,人格底线、伦理底线、精神底线裂缝已现,文明解构与文明结构的尖锐冲突已经如此严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一切真正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都有与其相匹配的具有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的人物先驱于荆棘丛生之地。创建人类社会文明,需要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大量涌现,弥纶八荒,亘带九地。千涛拍岸,当政治家和思想家面对不可回避的历史挑战,凝视历史,前瞻未来,思考如何去变革固有文化形态的转型;如何去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之时,也值得每一位中国艺术家以敏锐的触角和思者的使命意识去抚案而长思:如何以文化的力量去宣拓发扬人类生命的善性,以致爱致悯的人文情怀,去进行有时代意义的文化探索和艺术创造。
作为读图时代中图像之一种,绘画的意义何在?写字画画难道仅仅就是写字画画吗?道上者解蔽:照狗描虎,抄山划水,应物摹形,这只是从事艺术的最基本,还缺乏文化的高级含量。质言之,大专院校的艺术教育不仅是技法培育,更要有一种精神陶冶。这里我完全认定色、形、点、线、面作为中国绘画艺术语言的美学价值,技术上得心应手是成为一个名画家的必需才能,但更为难得的是在视觉背后注入人文气息。宋人说“画者,文之极也。”如果文化短板,最高成就也只能是一个二、三流的堂会画手。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从事艺术创作是需要人文思想的!艺术的创作者如果失去了人文思想,还奢谈什么艺术内蕴,更与“有思想的艺术”沾不上边!笔墨技巧的探索和充满趣味的表达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丰厚的思想储备,没有对艺术意义本质的洞悉,就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恒心,难以抵挡价值倾覆及市侩世俗潮流对高尚艺术精神的浸漫,在勾勒渲染、笔路盘旋时也就无法自由地掌握内在的律动节奏,滞行、踉跄或浮滑中不足以见灵气豁畅和意象生命的峥嵘,也难达境生于象外的雅逸境阈,不会具有大气象、大格局、大历史的精神承载。对一位人文艺术家来说,落落寡合、踽踽边缘时也应该是精神层面上的强势者,涓滴学思汇成浩浩精神大河,独立苍茫阅世态,天外有风吹海立,在人性的冰封地带开启苏醒的锁钥,不仅有梦想的勇气和更高的超越,其艺术追求要深入到艺术与生活、生活与思想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萦回纠结关系,并从中获得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感知。其经典性的艺术作品不会是某种程序模式的一再重复的快餐鸡汤,也不会局限于唱诗班的或低缓吟唱、或冕旒热闹。伟大的雨果在遗嘱中写道:“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我想,艺术家的文化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一个民族要成为伟大的民族,并不仅是树立起绵亘耸峙的水泥丛林,并不是从世界市场上赚了多少钱,而是有没有像星星一般众多的文化巨子在夜空中出现。举目环顾四周,无数精神流浪者挤拥在一个理想冷却的坎陷里,形成一个如同丧家之犬盲目追逐、相互撕咬又恶性循环的怪圈,尔虞我诈中失掉自我,不知道人的灵魂需要安歇、需要皈依,只剩得一身皮囊和抽干脑浆的头颅面具,双眼还显露出猎狩长夜的决绝和狠毒。不管瀚海百丈冰、愁云万里凝,不管前路有多少风霜、万千雷暴,不管满天黄沙,浮世千重变,大艺术家一定要关注人类灵魂的救赎命题,午夜神驰,弹剑为文,爱与恸似涨满的潮水,一枝孤笔万仞山,人微换得家国重。那是对社会环境进行人文思考之后的独特的艺术创造;是浪漫与叛逆,是抒情且唯美;是寒夜凉嗖时对生命的珍视,是心悸阵阵时对苦难的抗议;是干涸源泉废墟上开出的金色向日葵,是迎风摇曳中永不熄灭的生命火炬,是心灵深处震动后的簇拥倾吐;有时,甚至是匍匐在刀锋上的焦虑和煎熬的灵魂,无惧自己生命的消熔和枯草片片掩荒冢,急切地从精神上寻找人类共有的、潜在深处的人性,包括去揭示新的人类危机中怎样通过艺术来激活人们麻木的神经中枢!
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1924年就在北平以他的预言式的人文洞见告诫中国:“污损的工程在你们的国度拥挤不堪,污损的精神闯入了你们的心灵。假使你们竟然接受了这个闯入的怪物,假使你们竟然泯灭了你们伟大的天赋,竟然得意狂妄起来,那时候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人类文明正等候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灵魂的纯美表现,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中尽你们的贡献。”据我考证,“人文”一词,早就出现在专门论述世界万事万物变化之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中,《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此承溯,动荡的暴力杀戮到妇女裹脚到男子阉割的腐朽重压中,才有汉唐之气,宋明之情,中国历史文化的琥珀才更加绚丽多姿,面对生死义理与天道自然,个体生命之火如熊熊烈焰。从春秋战国遥遥相望的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从魏晋前有士林景致的建安七子,后有肆意酣畅的竹林七贤;从称病弃官修身养性、专研书法的王羲之;从“浩然而独存者乎”的苏东坡;从被称为古代十大家的顾恺之、李思训、王诜、米芾、米友仁、李公麟、倪瓒、王绂、徐渭、朱耷;从“只留清气满乾坤”的王冕;从成为宫廷画师又被逐出皇家画院的“浙派”开创者戴进;还有不被当时所谓的正统画派所认同,对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作风深恶痛绝,大开创新之风的扬州八怪等,这一理念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历代大画家、大艺术家的创作践行,促使他们抵抗势利化、庸俗化的潮流对心灵的压榨,在沉沦与救赎的交结中大胆脱离惯性轨道而诗意地栖居,同时又仁心己任、蹈义凌险,笔中肯綮,掷地论定,冲击旧有的制度沉屙和思想淤泥,不妥协的思考和关注时代的变革、民族的命运,在遭遇事业与生活的跌宕起伏、逆境挫折时,临难不苟,仍能以一种理想、激情的美学力量,突破僵硬迂腐的思维模式,喜怒哀乐地歌咏真善美。几千年前的屈原,依然影响着现代人的心魂,千百年岁月不会孤独,风风雨雨总关情,横向之于当代,纵深之于历史,审视之于深层,反躬之于自身,我们面对这些鲜活而有尊严的君子之光,有否听到冥冥之中先人英灵的呼唤?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又是否担当得起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传承者?存亡继绝正是我们的历史托命啊!卓越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位悲悯与担当、仁爱与正义、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践行者,具有知行合一人格矜式的敞亮光泽,从未曾停止对国家前途与民族精神的关切与思考,那是所有中华儿女的絜矩之道,那是中华民族一切艺术的镇石,携着它,可让艺术家免于没入虚无之中。也可避免艺术界在名利双收、觥斛交错、推杯换盏、鹂啭莺啼中成为社会腐败组成部分的溃疡。
当今几十年的社会发展速度,语言逻辑、生态环境超越了过去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进化意义上的人类在不停地向前行走,对艺术的内涵也会有新的人文维度、新的时代标尺,文化生机的勃发须从传统向现代的成功转化中光大起来。特别是整个社会在变革与转型时期,作为时代节点的人文艺术家都是能静观现实和坚持理想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现实世界的一分子,从而与自己生命的密切相关中,产生对现实世界的独特的心灵体验和感悟。真正的艺术家是历史的在场者,不会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自居。如果远离喧嚣的尘世追随慎独,丘壑情结,山水情怀,也是独立精神的自觉,在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悠然见南山,幽篁之长啸,施洗蒙尘的脾胃,旷达超逸中寻求最大的效应是发现自我人性,期盼离开被谎言所笼罩的世界,听见自己良心的声音,从而可以与自我展开更深层次的精神对话,如南宋著名文人雅士葛绍体诗曰:“堂深暑不到,闲意一炉香。棋斗过河急,琴弹流水长。古瓶疎牅下,怪石小池旁。忠献画图在,英声不可忘。”中国古代思想家与教育家孔子有名言:“行义以达其道。”但也许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那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氛围中,生怕隔墙有耳,被人告密,在不许说真话的岁月,人们任何讲真话的言行都存在被上纲上线为“政治立场问题”的危险,极左政治的文字冤狱对中国艺术家带来太多的灾难,职禠家弃,命运多舛,有的还亲身经历过现代的焚书坑儒,这致使那些曾怀有理想追求的艺术家在创作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趋向如履薄冰般的谨慎。对真理的不敢直视造成了对于现实的逃避,目前有不少画家认为远避社会世事矛盾,就是“超脱世俗”,还推诿辩舌是“得禅之人”。有的聊博一笑的自嘲中堕入了被抽掉内在德性与价值的“玩世现实主义”。在现代信息接受已经呈现出生态规律的今天,广义上,艺术介入社会学领域是艺术自身所承载的时代和文化责任的重要组成,对一个追求艺术意义的中国艺术家来说,能否创作富有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作品才是其实现艺术理想的重要指标,而世故玩世的心态则意味着“发达的头脑和萎缩的良心”,这也是源于人的生存自私,正是这种广泛的缺乏存在高度的自私构成了世俗社会的基础秩序,加上人都摆脱不了吃穿住行、生老病患的现实生活。所以,就人性而言,怯懦并非是不可理解的人性弱点。最不应该的是有的人总以自己病变虚无的姿态,以“平庸的恶”冷漠地去寒碜那些浮嚣俗世中难得一见的有灵魂、有良心的思想者、燃灯者,以皮皮赖赖的自私与沉默、以及唯谄、唯佞、唯假的助恶方式,默认各种社会道德无底线的滑坡。这是因为他们的思考能力远远达不到大艺术家的境界:“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自从头戴刺血荆冠、身背沉重十字架的耶稣在走向各各他山受难的路程中,喊出了犹太人当时并不理解的期许后,爱和悲悯,已经根植于全世界绝大多数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们的天性,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所有的大时代都处在危机潜伏的嬗递演变,作为一个独立思考、心灵自由的艺术家,在对崇高艺术意义的求索中,总是努力用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正能量,在邪恶与唯美两极对峙之际,在天地人心之间,迎着惊涛骇浪去抵抗和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对真善美的憧憬与追寻和艺术对历史命运的表现力度,更是杰出人文艺术家艺术作品的张力结构,当然,这样群类的艺术作品,经得起岁月的淘汰磨洗,唯存神韵流芳,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管是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等,都属于宇宙哲学和精神追问的范畴。日月星辰的升沉运行,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智慧与智慧为伍,理理相通,诚如骑着青牛西去的老子曰:“源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人类的主要道德体系都是与宗教信仰共生的,上述各种教义的真善美的最高峰上是有共通点的。纵观佛学源流,2600多年前,29岁的古印度迦毗卫国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为穷生死之理离家修道,于35岁在印度菩提迦耶开悟本性智慧,究宇宙生命之实相, 形成“佛法”,产生“佛教”,被人尊称呼“佛陀”。
(下转第3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