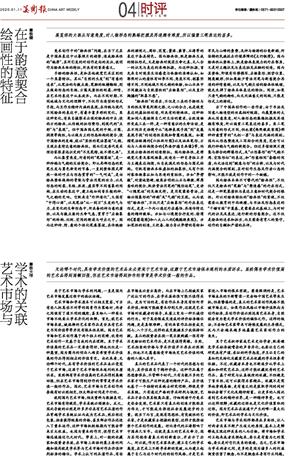绘画性的特征在于韵意契合
■杨健
展览体的大画从写意角度,对人物形态的熟练把握及再造颇有难度,所以偏重工笔表达的甚多。
美术创作中的“绘画性”问题,在当下尤其是中国画表达中以摹照片的趋势,造成绘画性的“缺席”,其所引发的对创作走向的关注,说明作为绘画本体的特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手绘的绘画性,是和其他视觉艺术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从“自然的生发”到“有意的追求”,从笔法的勾皴点染、笔触的纵横翻转,到点线面形态的长短、方圆及质性的刚柔、神情,在艺术的表达中从未放弃。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与文化的理解中,不仅作为造型的形式手段,而且作为精神内涵的表现,在传统与现代不同绘画的表达中,有着丰富多彩的变化。虽这种变化,有来自摄影术出现对绘画的冲击,使西方的绘画,从传统的拟形塑形,到现代的“点彩”与“表现”。但中国画因毛笔的中侧、方圆、润涩等线性,与以线为主的形态结构的契合,使中国绘画的发端,就以“显性的笔法墨迹”之韵,呈现出表情达意的绘画性。因而引发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识定的“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
而从鉴赏角度,所看到的“笔踪墨迹”,是一种神韵与气韵的生动契合。即从局部形态的笔笔生发与墨色渐变的节奏,一直到整体图式浑然一体的呼应与形态贯穿的“一气呵成”,是由绘画整体线构的骨架与骨法用笔的功力,以及形态的刚柔、长短、浓淡、虚实等不同意象的同构,在生动的表达中,建立起如同音乐般的神、气之韵的交响。它既来自“外师造化”,又须有“中得心源”,以及笔法“从一到万”生发的气与力,在变化的生命形态中,所具备的神与意的质性,以及勾皴点染的生命气息,贯穿于“应物象形”的结构、比例、空间的断连与呼应之中。因而这种神、情、意的个性化笔痕墨迹,在传统绘画的顾恺之、周昉、范宽、董源、龚贤、石涛等的表达中各具特色。因而绘画性,既是绘画生成的特征形式,又是绘画对现实生命之真,天人合一的识见与表达的准确把握。而这种把握,首先来自对现实生活感受与体验的准确认知,如郭熙对山的质性有四季不同、角度不同、朝暮阴晴不同、不同地域不同之韵的体验,如山水画中不同皴法与自然质性的“应物象形”,以及直抒胸臆的“取象不惑”。
“绘画性”的存在,不仅是工具的手绘性与目的性及审美判断之眼、之心的合力,也是视觉表达的虚拟性创造,所具有的特殊性。这种结果如同人类按照自己对生活的需求,去改造物件变成工具一样,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从“选择表现手段”到“发展表现手段”的创造性实践和智慧的展现。如粱楷笔法淋漓的《六祖砍竹图》以及油画笔形、方向与人面结构契合的《弗洛伊德自画像》等,均呈现出绘画性的创造特征。因而绘画性,是将视觉元素及客观物象,改造为一种自身独立并与主题表达相契,而自我满足的形态与图式结构。它既有绘画本体虚拟的抽象性,又有个性对客体物象认知与再造的重组性。亦如“斧劈皴”,对质地坚硬、棱角分明的山石与雄健、浑厚意味的契合,既讲骨法用笔的“随形运笔”,更讲“心随笔运”的见物见情。是用笔需要骨法,应物必须象形的“神韵”及“气韵”的呈现。从而说明“绘画性”,不仅只是“应物象形”的外在表达形式,更是一个内心通过外在感悟、再造传情达意的精神载体。亦如与心境契合抒发的、徐渭的《墨葡萄图》和八大山人的《鹌鹑游鱼图》。亦如笔性的创造,王迎春、杨力舟以斧劈的苍劲和军民与山峰的叠塑,及神与物游的壮美新韵,所熔铸的民族抗击外侵屏障的《太行铁壁》。因而绘画性从整体上,既是绘画表现力的外在彰显,又是对主题识见与表达独见共融的创造。因而其整体,即便有传移模写、应物象形、经营位置、随类赋彩,但如果缺少骨法用笔与新意契合再造的神情意韵,以及与气韵生动的绘画性统领,就先失掉了绘画本体表达的特征。同理,如果只看气韵的趣味,而无内涵意义的同构,只能是形式上的游戏。
当下中国画创作的一些作者,由于书法及写意人物造型的功底相对较弱。而展览体的大画从写意角度,对人物形态的熟练把握及再造颇有难度,所以偏重工笔表达的甚多。虽工笔与写意的形式不同,但也需《韩熙载夜宴图》那种神意贯穿的“九朽一罢”与表达内涵的深刻。因而从形态塑造及工写结合的角度,完全可以践行神韵与气韵的新契合。但过多借助照片搜集与拼合的群像形式,及“以形摹形”的“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的表达,和“形意相同”套路的同质,而无法达到“赋意与形”的出新,以及与时代内涵契合的深刻,其对创作生态及作者心态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创作中的一个缺憾。
因而绘画本体不可替代的“绘画性”,不仅仅只是绘画的“笔触”与“塑造感”的外在形式,还是一种笔墨质性与表达立意和时代契合的根性。所以对绘画特征的“绘画性”的重视,不仅需要从教育的中西碰撞,与书法及形态表达的“千锤百炼”中奠基,更需要在此基础上,与对时代的识见及表达,进行新的形意契合。这不仅是绘画的追求和担当,而且需要有育人的坚守,创作的自醒和严谨的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