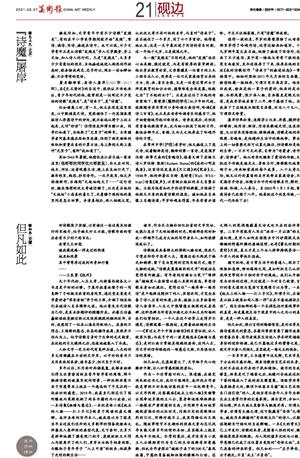“诗魔”屠岸
■包立民(北京)
据我所知,文学青年中有不少诗歌“发烧友”,有的在中小学求学期间就开始“发烧”,背诗、诵诗、写诗,痴迷在诗中。也可以说,不少文学青年正是从诗歌“发烧友”步入文学殿堂、步上文坛,加入诗人的行列。凡是“发烧友”,又多多少少有类似的经历,当他痴迷地进入构思创作状态时,就会物我两忘、忘乎所以,闹出一些如醉如痴、不合常情的笑话。
著名翻译家、老诗人屠岸(1923年-2017年),在《生正逢时》的自述中,就供认不讳地承认,青少年时代的他,就曾经是一位闹过不少笑话的诗歌“发烧友”,是“诗呆子”,是“诗魔”。
比如读高三时,有一天,他正在理发店里理发,心中默诵英文诗。突然领悟了一句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诗中的妙处,就兴奋地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惊得理发师傅目瞪口呆。同学们知道了,为他取了“尤里卡”的绰号。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在浴缸里洗澡,悟到了测定物体的体积和重量关系的计算方法,马上奔到大街上高呼“尤里卡”,意即“我知道了”。
再如1943年暑期,他借住在江苏吕城一家米店里(他哥哥的同学沈大哥家里),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坟旁观察生活,晚上在豆油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抄写诗作。一次半夜里,他大声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了……”这句诗时,睡在隔壁的沈大哥被惊醒了,以为是当地的“天地坛”小庙真的着火了,光着膀子跑到他的屋里问是怎么回事。弄清真相后,两人相视大笑,从此沈大哥不再叫他的名字,而直呼“诗呆子”。在吕城住了一个多月,写了六十多首诗。他得意地认为,这是一生中最沉迷于写诗的苦乐时期,这一年他十九岁,正是弱冠之年。
与一般“发烧友”不同的是,他的“发烧”决非心血来潮,烧过就完,而是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出身在教育世家,父亲蒋骥是一位留日的土木工程专业人士,母亲是一位旧式家庭培育出来的才女,诗、画、音乐全能,又是一位受过常州女子师范教育的知识女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敬之为“了不起的女子”。正是在这位了不起的母亲熏陶下,蒋璧厚(屠岸的学名)从少年时代起,就跟随母亲用常州口音吟诵古典诗词,吟诵《唐诗三百首》,也正是在母亲吟诵音乐的感召下,他开始偷偷地作起旧体诗来。母亲发现后,非但没有责备他耽误学业,反而细心批改了他的习作,教他分辨平仄、音韵,久而久之他养成了吟哦作诗的习惯。
在常州中学(沪校)求学时,他又痴迷上了英文诗,试着翻译英诗,翻译的第一首诗,是英国罗伯特·斯蒂文森的《安魂诗》,接着又译了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我的心啊在高原》,这首诗还发表在《文汇报》的《笔会》上,1948年,他的译著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诗集《鼓声》,以青铜出版社的名义自费出版。正因为他有如此中西诗学的渊薮,才保持了他经久不衰的热爱诗歌的温度。诚如他在自画像上自题诗道:早岁吟哦未得篇,年来苦索亦堪怜。平生不识烟茶酒,只有“诗魔”伴我眠。
值得一提的是,早岁的蒋璧厚除了从母亲那里学得了吟哦作诗,还学过绘画和速写。十九岁那年夏天在吕城,他除了痴迷于写诗外,还画了不少速写,其中有一幅他与哥哥下棋的炭笔自画速写,至今还保存了下来,保存在他的自述《我的诗歌创作·“诗呆子”的痴迷状态》一章插图中。细细对照他2011年元月画的自画像,脸型轮廓一脉相承,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他告诉我说,绘画是他一辈子的爱好,他画的是水粉、水彩风景,很少画人物,自画像更是绝无仅有,是我苦苦地求索了二年,终于感动了他。为我画下了这幅炭水钢笔自画像,时为八十又八,可谓弥足珍贵。
屠岸信奉杜甫,追踪莎士比亚、济慈,膜拜诗神缪斯,他写诗、译诗,用诗来歌颂光明,追求理想,又以诗来消除烦恼,驱除病痛,诗歌是他的安眠药、安魂曲,是他精神生活中的维他命。事业上的一切荣誉光环可以置之脑后,但诗歌却是他的生命,一日不可无此君,自命为“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他从母亲处继承了爱诗的传统,又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熏陶子女,传承给家庭的每个成员。八十大寿之际,他又以外孙晨笛的名字来命名家庭诗会,不定期召开诗会,环绕古今中外的诗歌名作,解析、朗诵、吟诵,人人参与。自2003年1月1日起,家庭诗会已延续了八年。他要把这个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