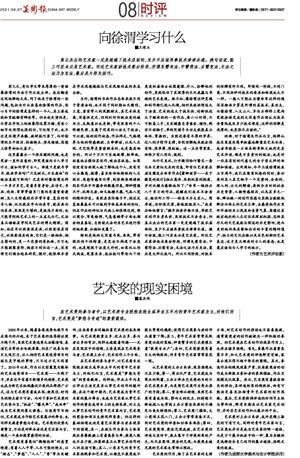向徐渭学习什么
■王进玉
前几天,有位学生带来厚厚的一沓临摹徐渭的书法习作让我点评。我边翻看边同他聊起天来,问了他关于徐渭的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会喜欢徐渭的作品,你心目中的徐渭是怎样的一个人,其主要成就和贡献都有哪些等。但令我失望的是,尽管在字形上他临摹得还算不错,有些小细节处理得也很到位,可仅限于此,也不过是依葫芦画瓢、徒研技巧罢了,而对徐渭的生平经历、性格特点、涉及领域、思想主张等却知之甚少。
这里暴露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是笔者一直所在意的,即究竟该向古人学习什么,该如何学习古人。难道只是就书学书、就画学画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真就可取吗?尤其面对像徐渭这样一个多才多艺,有着多重身份,在诗文、书画、戏曲、军事等诸多门类均有着重要建树,且人生情感经历异常丰富、复杂的传奇人物,仅仅就其字而论其字,就其画而论其画,显然是不够的,是肤浅片面的,也只能学到他艺术上的一点皮毛而已,无法真正领略其学问及艺术的博大精深。须知,论其书必然要谈其画,必然要谈其诗文,必然要谈其戏曲,它们是一脉相承、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不可也不能割裂看待,倘若不明白这一点,没有将它们综合起来研究、探讨,就很难弄清其学术思想路径与艺术风格形成的来龙去脉。
另外,徐渭的书画作品总体来说不同于晋唐法帖,也不同于同时期如文徵明、王宠、唐寅等人的风貌特点,其艺术性更高,写意性更足,但同时对传统法度的破坏力、反叛意识也更强,带有浓重的个人情绪色彩,且属于明显的心法大于技法。可以说,他的创作状态、作品样式、气格境界与他的情感跳跃、生命律动,以及人生观、文艺观等是紧密联系的,也是高度吻合的。所以千万不可东施效颦,轻率地、刻意地去模仿其创作,效法其状态。如果你没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这个人,没有用心去熟悉、揣摩,甚至体悟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变化等,则很难准确捕捉到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敏感信息,那种愤懑不平、沉郁无奈,却又纵横不羁、气吞八荒的精神抒发。虽然在实际练习中,经过反复临摹基本可以做到字体或画面的形似,但在作品的神似与内涵上却很难达到,难以契合,审美格调、气息意韵等方面也都会相差甚远,自然就无法对其艺术进行很好地承袭、弘扬和发展了。
特别是他的大写意书风、画风,带有强烈的个性特质,是完全不拘泥于法度的,也是超脱于法度之外的,如果仅从形式构成、笔墨关系、技法技巧等形而下的角度和层面去试图窥探、介入、诠释他的创作,显然低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表现。殊不知,像徐渭这种灵魂和创作都已进入化境,相对来说性情远大于法度、艺术性远大于技术性、创新性远大于继承性的一些作品,要小心对待,不可轻易上手,且关键靠自身意会、领悟,绝非不动脑子,单纯凭借手头功夫就能真正体味、掌握的。当然还要有丰厚的学养、过人的才情作支撑,否则理解起来就会很有限、很单薄、很刻板。这一点非常重要,却很少有人明白、做到。
而行文至此,打开微信恰巧瞥见一条与本文看似无关的消息,即有位艺术家在朋友圈发出冷军作品《蒙娜丽莎——关于微笑的设计》拍出高价、再刷纪录的报道,并对此颇为感慨地写下:“冷军一幅拍出八千多万的作品,提醒我们技术不会老去,做任何工作——称圣不斥大匠人。简单说,活好很光荣,要做就做匠人。”我看后给他留言:“撇开拍卖价格不谈,单就艺术创作本身来讲,虽然技术不会老去,但真正杰出的艺术家一定是超越了技术层面的,至少不应该再拿技术津津乐道。换句话说,能工巧匠未必是艺术家。何况艺术家讲技术要分阶段,所谓先需有法、中需得法、后需变法,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最后是大师无技巧。所以不同阶段,对技术的理解有所不同。即便同一阶段,不同门类、不同画种对技术的要求和体现也大不一样。一般人可能认为像冷军这样的超写实绘画才算是所谓的真技术、真功夫,而像徐渭、八大山人、齐白石那样三笔两笔就涂抹完成的大写意作品便认为技术含量低或没多少技术难度,这样的理解是浅薄的,也是很不应该的。”
的确,对于徐渭及作品而言,纯粹从技术角度来简单粗暴地衡量其艺术水准,或者单就某一方面来断章取义地判定其艺术价值,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对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才型大师的曲解和误读。众所周知,今年正值徐渭诞辰五百周年,我们在隆重纪念的同时,务必要对其人其艺给予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深入的、公允的解读,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人物情感经历,以及其多元一体、辩证统一的创作思想与实践去致敬他鲜活而伟大的艺术生命,去感受他作品里所洋溢的名士风度和圣贤气象,要透过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过往来深刻把握、总结其非凡的文艺成就与深远的历史影响,进而更好地传承其留给后世的丰富的精神遗产、独立的文化品格以及本色创新的艺术表达,这才是正确面对古人的姿态,也是最应该向古人学习的地方。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