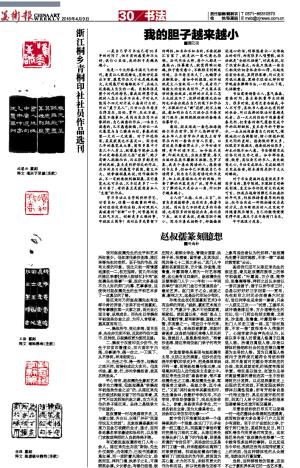赵叔孺篆刻臆想
■听雨轩
■听雨轩
我对赵叔孺先生的生平和艺术所知甚少。但知道他是沙孟海、陈巨来等先生的老师。至于他的作品,没有太深的印象。因此只能一厢情愿地臆说一二,权充抛砖。前几年出版的陈巨来著《安持人物琐忆》中有“赵叔孺先生轶事”一篇,说的大多是些不为人知的师门内幕、艺事掌故,这使我对赵叔孺先生的生平和艺术多了一点真切的了解。
陈巨来对乃师赵叔孺先生有这样中肯的评语:“自来不论书画篆刻,苟专事模仿某一大家之派,而无自己面目者,总难成名。而先生以学撝叔卒能继吴缶翁之后,为印人首领者,盖其原因有三:
一、撝叔所作,变化多端,面目至多,先生亦无所不能,且其所作仿六国币、汉封泥,以视撝叔更为挺而且稳;
二、撝叔于汉凿印至少仿作,先生于汉官印最擅长,汉六面印中白笺、启事诸作,偶一仿之,一刀既下,从不修润,神采奕奕也;
三、先生之作,得一秀字,与撝叔之浑不同,故得能成此大名耳。但其书法,篆、隶、行,亦均学撝叔者,故其名稍逊矣。”
平心而言,赵叔孺先生篆刻艺术确乎功力精深,但赵叔孺是“学撝叔卒能继吴缶翁之后”的,从陈巨来先生的叙述和赵氏留下的作品来看,其才气不如其师法的赵之谦,功力不及他的弟子陈巨来。总体上是继承大于创造的。
赵叔孺曾一时与吴昌硕齐名,又与黄士陵、齐白石、王福厂并开“民国印坛五大流派”。且赵叔孺是篆刻书画乃至金石收藏的全才、通才,因而各地慕名来求墨迹和治印的,以及登门求教或拜师的人自然络绎不绝。
有记载说赵叔孺所收门人有60余人。陈巨来先生则说“斯际,先生外仗梁势,内依婿力,已视书画篆刻蔑如焉,而一班附庸风雅的仕女,纷然而至,拜列门墙,执弟子之礼,可谓群英杂凑,少长都全,有银行经理、钱庄阿大、朝鲜女学生、青楼女画家、纨绔子弟、没落者、留学者,及其没后,闻共得七十二贤之多云。”其门人中篆刻名家陈巨来、方介堪、沙孟海、张鲁盦、叶露园等人都为一时艺林翘楚,这也是有目共睹的。赵叔孺先生还曾率领门人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举行“赵氏同门金石书画展览会”,轰动艺界。赵门弟子之众,成就之高,影响之大,这是近代印坛少有的。
孙洵先生在《民国篆刻艺术》中有这样的评说:“诚然,篆刻艺术虽方寸之中,气象万千,孰不可论某家高,某家低。然民国以来,‘吴派’显占上风,写意抒情,颇有新鲜感,遂趋之若鹜,亦因素之一。唯近四十年代来,仅上海一地,学吴派者寥寥,学赵时者甚多,这自然与陈巨来等人印风所染,造就后人,是息息相关的。”再看沙孟海、陈巨来两位赵门弟子的有关论述:
沙孟海曾将吴昌硕与赵叔孺有太阳、太阴之比的美誉。但沙氏在他晚年所蓍《印学史》中,把吴昌硕单独开列一章,而将赵叔孺与徐三庚、王福庵并列归入近代细朱文名家之中;陈巨来先生则说“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稳;尊叔孺先生者,辄病昌老之破碎。吴赵之争,迄今未已。”又说“其时余尚学其篆法刻印,先生谓余曰:你最好专学汉印,不必学我,学我即使像极了,我总压在你头上。你看,吴昌硕许多学生,无一成名能自立者,因为太像昌老也。自后余即以专仿汉印为事……”
就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赵氏门下几乎全是一派工谨之风,而偏重于章法布置的完美与刀法的工致。从陈巨来先生等众多门人留下的作品看,即便是所谓的“专仿汉印”,其实走的也还是师门工谨一路,并未超越和出离师门的审美范畴。抑或赵叔孺当时确也看到了门派观念的负作用,然而因为其心量、才力的不足,未能有更大的作为和改观。所以我觉得他还称不上象有些论者认为的那样:“赵叔孺先生善于因材施教,不求一律”“卓越的教育家”云云。
甚或我们还可从陈巨来先生的叙述里,睹见赵叔孺在教学上的保守和偏颇:“叶露园、方介堪、陶寿伯、张鲁庵等等,拜师之后从未尝以一语训迪诸子,诸子以所作求正时,总是以好好好三字回答……更有,先生刻印之时间必在凌晨六时左右,故任何学生总未尝一睹者,只余一人获见三次……”试想,工稳印风或许确是陈巨来、方介堪等先生的优长,但一门师出包括支慈庵、戈湘岚、沙孟海、张鲁盦、叶露园等一大批门人尽走工谨一路,这“因材施教,不求一律”就很难令人信服的了。心理学家许金声先生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普遍人格属于归属型人格。所谓归属型人格,即是以群体的接纳和社会的适应等归属需要为主导的人格。因为归属型人格倾向于怎样使问题符合传统和群体,而不是面对问题去寻求相应的办法,故其成就动机的强度有限而早衰。特别是以独立、创造为主导的高级需要的潜能在其一生中没能得到充分发挥。以此观照篆刻史上出现的艺术流派,不难发现这样的群体归属性现象:所有开派者自是一代特立独行、具足创造开拓的宗师,而其门人弟子则多半会把继承因袭看得比创造开拓还重要。
尽管宗派和流行印风可以使得一时一地的整体水准得到迅速提高,然而效仿者大多会囿于门户之见而少有进取。至于斤斤在派别之争、计较于师门地位,甚或师生反目,同门倾轧等负作用更是时有发生。这在陈巨来先生“赵叔孺先生轶事”一文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以此反观当今印坛,虽然还没有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流派,但这种群体性的从众随流,依然在风行蔓延着。
当然,这种群相效仿现象,还远不止于篆刻界和其它的一些艺术圈。